【探尋古道】走讀南澳 泰雅族尋根之路|華視新聞雜誌
宜蘭縣 / 徐敏娟 採訪/撰稿 張書堯 攝影/剪輯
南澳古道,過去是泰雅族人往返 宜蘭 大同鄉四季與南澳間的山徑,沿途可以看到當時的部落地點,耕地和獵徑。日治時期,日本人為了控制泰雅族人,在山徑上開闢了多條警備道,至今還依稀可見人工鑿路痕跡,和穿越河流的舊吊橋,如果走到警備所遺跡,還有不少日本製的廢棄酒瓶。2016年,泰雅族更有一對 青年夫妻 韋浪和比穗,選擇回到部落的土地,親手蓋起了家屋,希望重拾傳統與記憶,充滿故事的南澳古道,一起探訪。
傳說,泰雅族人源於南投仁愛鄉,祖先從大石頭蹦出,在四周建立部落。隨著族人越來越多,開始踏上遷徙之路,到思源埡口。相傳泰雅三兄弟,大哥Kbuta越過大霸尖山,向西部移動。小弟Kmomaw順著蘭陽溪,定居現在的宜蘭大同鄉。二哥Kyaboh翻閱南湖大山,落腳和平溪流域。泰雅族群在台灣的分布,大致成形。
走在幾近原始的山林古道,還有潺潺小溪流經。我們跟著宜蘭縣史館廖英杰館長,和文化局文資科同仁的腳步繼續前進。這一路並不好走,非常濕滑路又狹窄,還只能一個人通過。茂密橫生的草叢,快要覆蓋讓人通行的道路,這裡是位在宜蘭南澳鄉登山路徑,南澳古道,這段路也存在一段,關於泰雅族女孩莎韻的故事。
宜蘭縣史館館長廖英杰說:「這個地方就叫做莎韻橋,以前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,有碰到當時80幾歲的Hayung(哈勇),哈卡巴里斯社的一個長輩。因為他當年跟著莎韻,送行老師的隊伍一起下來,走到這邊的時候過溪的時候,莎韻就因為水很大,所以她不小心失足掉到水裡,Hayung(哈勇)告訴我們,就是在這個地方掉下去的。莎韻當時在南澳南溪遭難以後,後來日本人幫她立了一個紀念碑,愛國乙女莎韻遭難之碑。」
特別建立紀念碑留存至今,但對當地的泰雅族人來說,是一段時代悲歌,甚至成為日治時期,皇民教育的範本。
廖英杰說:「轉化成學生對老師的情感,然後這樣的一個故事又把它描述成,台灣人或者原住民,對於日本天皇的效忠的故事,就被轉譯成是一種皇民化的教育,還把它拍成電影寫出曲子出來,好像是一個很浪漫的故事,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。在泰雅族裡面,他們其實很尊重傳統上,gaga(泰雅族信仰)的概念,就說師生戀這種事情,對他們來講其實是不太應該存在的事情。一直這樣描述,其實很多他們的後代會覺得,跟事實上是不符合的。」
泰雅族的文化,部落獵徑及耕地遺址,和當年日本統治時期,留下來的警備道、駐在所遺跡,在3公里長的南澳古道上,隨處可見。廖英杰說:「南澳山區的日本警備道,基本上就是一個人字形,北邊就通往寒溪,東側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,從南澳平原進來位置大概在這個地方,西側是從大同鄉的四季部落進來。最後3條路會在流興部落,大約這個位置會合,基本上開路都是為了要控制部落,不然不需要開路,哥各朱跟奎諾斯這兩個部落移走之後,這條線就沒有再用了。最早的人字形,北邊這條是1919年做的,東側跟西側,大概是在1922年完成的。」
廖館長口中的人字形警備道,是現今貫穿宜蘭南澳和大同鄉的比亞毫古道。1919年闢建,東起南澳村,西至四季村,還有一條通往北邊的寒溪村,全長將近90公里,主要通過南澳泰雅族,15個傳統部落領域。
廖英杰說:「這一個人字形的警備道,中間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分叉的路線,日本人對於這些分叉地區的部落,他其實會專門開一條警備道去管理它。可是當這個部落遷走之後,它這條路就廢掉了它就不用了,那駐在所也會撤掉。」
警備道,是日治時期為了管理泰雅族人,集團移住的理蕃道路。廖英杰說:「基本上南澳古道它是日本人開的,有一小部分是利用泰雅族人,舊的社路去開成警備道。我們發現,原來日本人之前,泰雅族的舊路,其實在這個地方可能存在300年了,但它的歷史價值,比日本警備道更重要。」
歷經日本統治,南澳古道上留下許多當年的遺跡。廖英杰說:「日本警備道,當他遇到石頭的時候,就會盡可能把它鑿開來,為了讓員警或軍隊可以快速移動。這跟一般登山路線不一樣,像那個石頭,它應該是凸出來,可是它為什麼凹進去,這麼平的面其實有被鑿過啊。你的肩膀在走路的時候不會去撞到,搬東西你也不會撞到,下面也可以看到,有兩排人為的石頭,這就是泰雅族傳統上,他們作為耕地的工法。」
2022年10月初,因為連日大雨,造成南澳古道多處土石坍方,目前暫停開放。華視新聞雜誌採訪團隊,特別發公文申請,由專家帶路才能一探古道。記者徐敏娟說:「現在這樣子可以看到,南澳古道這邊有很大片的坍方的現象出現,也因此現在南澳古道是暫停對外開放,禁止民眾隨意進入。」
一整片大面積土石崩壁,距離下方南澳南溪至少10層樓高,沿途偶有碎石滑落,我們走得小心翼翼,深怕一個大意,恐怕滑落河床。好不容易通過膽戰心驚的大崩壁,挑戰還沒結束,我們必須脫鞋涉溪,才能走到距離最近的駐在所遺址。
廖英杰說:「這個地方地名就叫合流,這條溪叫合流溪,它下面就是南澳南溪,所以兩邊會匯合。這邊下面有個大瀑布,以前日本警備道,在上面最高點的地方,有一個合流橋,跨過這一條河,再到上面的駐在所,就是楠子駐在所。這裡是它的入口,入口會有個階梯,以前是一個木造結構的房子,在這邊兩面是它入口,會用石頭疊出一個地基出來,這個大概是離平地,最近的一個駐在所,特別是它還有鋪水泥,70、80年以上應該是有。」
遺址除了水泥地基,還有當年,日本製玻璃酒瓶。廖英杰說:「它寫台灣專賣局,這是日本時代的酒瓶,日本時代的酒瓶,基本上它有些特色。比如說很多是青色的,像他們清酒啊或者啤酒,或者是深咖啡色,這支就很清楚是寫日本啤酒公司的名稱,所以在日本時代,很多酒瓶上面,都會打上公司的名稱或是圖案。」
南澳古道的起點,旋檀駐在所,是日治時期的派出所,也曾是泰雅族舊部落遺址。廖英杰說:「旋檀駐在所,它原本它的周邊就是旋檀部落,旋檀部落就是,我們剛剛通過金洋的時候,有一個叫奎諾斯的部落,後來搬到這邊之後就叫做旋檀。」
距離旋檀駐在所0.5公里,是日本人建造,為了穿越南澳南溪的旋檀橋。廖英杰說:「像這個橋叫旋檀橋,橋的日文假名就寫旋檀,等一下下面可以看到旋檀橋舊橋的遺址,那舊橋的鋼索還在,它已經昭和5年到現在,1930年到現在。」
帶著傳說跟隨部落青年,踏上尋根之路探訪泰雅族,韋浪是泰雅族青年也是部落獵人,現在是金洋國小體育老師,南澳古道的山林,對他來說再熟悉不過。泰雅族青年韋浪Wilang說:「對於這條古道,我覺得我是熟悉的,我覺得這是我家,這一條也算是南澳群的泰雅人,在集團移住的時候,祖先曾經走過的一條古道。1912年開始,是南澳群的泰雅人離鄉背井的開始,南澳古道的起點,就是日本人他要理蕃,開了一條貫穿各部落,這個交通的要道。」
對韋浪來說,南澳古道的起點,也象徵泰雅族文化被迫終結的開始。1895年至1945年,日本政府以高壓管理泰雅族人,逼迫他們歸順。Wilang說:「民國19年這個橋通行,其實日治時期,他就已經把所謂的蕃界圖,譬如說南澳蕃南澳群活動範圍,大致已經劃定下來了,真的影響是我們對山之間的關係。泰雅族本來就是山的小孩,很了解森林自然,被殖民之後,這個東西你必須強迫地被放棄。」
泰雅族人的部落、生活方式被強迫放棄,使得傳統文化漸漸消逝,但記憶和存在過的印記不會消失。Wilang說:「生活的過程當中,一定會帶著孩子去認識他的獵場他的古道,過去是住在這個平台這個地方,它是一個腹地,老人的記憶他們口述歷史,日本人的紀錄,他們曾經住過在這個地方。你只要看到楓香林,大概就是部落要不然就是耕地,透過這樣子一個模式方式,他去規範了你的生活的領域,他要管理裡面的泰雅族,所以他開闢了一條日本的警備道,當然會沿用一些泰雅的古道。」
對韋浪輕而易舉的古道,對我們來說險象環生。Wilang說:「以前我小三到國中的時候,去種香菇用跑的。」韋浪突然有了驚喜發現,一瞬間已經站在邊坡的樹上。泰雅族青年韋浪WilangVS.記者徐敏娟說:「(老師你現在是在拿什麼),這可以吃喔,有點苦苦的,這就是黃藤,黃藤不僅可以吃,又可以拿來做我們生活的用品。」
跟著部落耆老,學習被遺忘的傳統文化,無論打獵還是口簧琴,他希望能透過自己傳承下去。他在自己的土地上,親手蓋泰雅家屋。Wilang說:「蓋家屋你要具備的材料就是木頭,竹子石板再來黃藤,立柱還有橫梁的部分,大概都是要採集檜木。那個檜木不是去砍它,是颱風天的時候,河流旁邊堆積的一些檜木,主要是採集那些東西。在我們泰雅屋,最上面這層都是用石板把它壓著,從小一進到山裡面,我就感覺到很熟悉,因為那是我的家人帶我去的,那時候馬上就跟土地上的,跟過去他們的記憶,生命的記憶連結是很快速。」
韋浪承襲泰雅祖先留下來的觀念,和自然共生、共好。Wilang說:「這個地方就是要煮東西的地方,上面都會放一些我們的生活的用品,放在上面,我們在家裡煮東西起火的時候,它會用一種,類似像燻乾的方式。」
韋浪搶救泰雅文化,展開尋根之旅也有了意外發現。Wilang說:「這個是泰雅族的名字嗎,對它用日本人的拼音yuraw mawi,我的外婆的爸爸叫yuraw mawi,哈卡巴里社的頭目。」
充滿泰雅族文化,和日治時期統治軌跡的南澳古道,儘管物換星移歷經部落遷徙,對泰雅族人來說,依然是泰雅族人的根,是起源地。而探尋古道,也像走入時間廊道,看見台灣在地的故事。
相關影片推薦
1:18
具荷拉鉅額遺產媽媽拿不到! 判決出爐網友狂讚:遲來的正義娛樂星聞160,199 次觀看・17 小時前1:44
還清白!新北旅行團食物中毒 白河磚窯雞驗陰性東森新聞影音1,306 次觀看・8 小時前1:56
震撼花觀光!海鮮店推龍蝦便當 民宿出清家具止損華視影音11,980 次觀看・4 小時前0:48
台鋼女神安芝儇超高人氣 代言手遊秀火辣熱舞民視影音2,184 次觀看・1 天前1:09
雷!《淚之女王》八點檔劇情反轉到讓人傻眼 最後這幕網友氣炸:到底在幹嘛?娛樂星聞5,833 次觀看・8 小時前2:00
"虎媽"載女兒突失控飆罵 趕下車要求當街下跪民視影音29,948 次觀看・10 小時前1:57
陸贈「組合屋」 林右昌:不是每個災民都想住TVBS新聞網影音921 次觀看・8 小時前1:23
雪霸大鹿林道湧成千上萬"馬陸" 綿延約50公尺民視影音2,681 次觀看・5 小時前1:26
女長期睡機場又大鬧國門 不聽勸阻遭警驅離東森新聞影音368,358 次觀看・3 天前
熱門必看
1:18
具荷拉鉅額遺產媽媽拿不到! 判決出爐網友狂讚:遲來的正義娛樂星聞159,932 次觀看・17 小時前11:37
地震不斷...我住的房子安全嗎? 達人分享最容易倒塌的5種建築Yahoo創作摩人31,753 次觀看・5 天前8:10
回家鄉過年,在馬來西亞剪頭髮,貴嗎?第一次看過這樣開椰子,嚇到了!芭樂媽的家 Qistin Wong TV2,606 次觀看・1 週前7:12
一哭就抱會寵壞寶寶嗎?這樣抱不僅可以培養安全感!也不會養成壞習慣!茜茜 育兒生活好好玩2,302 次觀看・1 週前11:23
多益聽力實戰必備技巧!小心這些陷阱題!【英文易開罐】從零開始考多益EP9英文易開罐23,087 次觀看・1 週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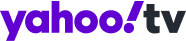
 Yahoo TV
Yahoo TV